软枣,黑不溜秋,圆中稍椭,形象委实不雅。我却对这极不受看的伙计情有独钟。
儿时,每逢邻村是集,便有一对一般高的小哥们俩手牵手溜去赶集,在逢拥人群的缝隙里钻来钻去,紧挽手臂﹑勾肩搭背,一刻也不分开。小哥俩瞅瞅这看看那,来回转到处钻,终于挑定了一处卖软枣的小摊,才亮出拳里攥得汗津津的两枚五分硬币。那时的一毛钱可了不得,一分钱就可买来一颗含在嘴里许久不化的硬糖。转眼间,我和哥哥的衣袋几乎全装满了软枣。走一步朝嘴里扔一颗,嘴巴一张一翕,随即" 噗噗" 射出几粒硬核,那神气及当时心里美滋滋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。软枣很甜,这是对儿时最甜美一种印记。
此情此景,一晃已二十几年过去了。去年腊月二十三是小年。按乡下的风俗要祭灶神。神虽小,一日三餐却与其瓜葛不开,可谓神小鬼大。因此,仪式是极其郑重当作大事来办的。灶台上燃上香,摆上几碟像样的点心糖果供奉。每年的供品里总少不了我最爱吃的软枣。这是母亲心里最清楚每次必备已成了惯例。这也是我最心急的时刻。供奉是神圣的,非得等到香完全燃尽了才能撤下来。我哪有了吃饭的心思,急急吃几口赶紧下来,眼瞅着香的进度。燃的太慢太慢了,心里不停地叨含着企盼着……多年在外工作,好几年没有回去过小年了。这次母亲来了,自然由她来操办祭灶神。有现成的几样糖果,想不用像以前困难时那样费力筹备了。母亲已经上了年纪,做这一套祭神礼节依然一如既往地认真,程序上一丝不苟。燃尽香撤下供,发现丰盛的供品里竟有软枣。妻又把软枣在水龙头下洗了又洗冲了又冲,再用开水烫一遍,干干净净地盛在盘子里。我贪婪地伸手就抓,心想:久违了老伙计,多年不见了。其他人对他却显不出丝毫的热情。
现在,可能不只是我,几乎沾染了洁癖。儿时的小哥俩从兜里把软枣扔到嘴之前,顶多用手指一捏一撮,吃得津津有味。如今这个菌那个毒的名堂多了来的也多了,买来的东西能削皮的削皮,不怕烫的热水消毒。才敢吃,吃起来才放心。
这应该说是件好事,尤其是经历了" 非典" ﹑面临了" 禽流感" 以后。但看看眼前经过几番" 洗礼" 的软枣,爽洁得几乎油光可鉴,我丝毫没有了食欲。
总有些东西是稍纵即逝可遇难求的。软枣的时代可能已经过时且一去不返了,而那纯真﹑美好﹑朴朴实实的童年往事却在记忆里青春常驻!
Articles by Zhang Xuesong (雪松)
Ĉu ekzistas viruso en EK - la esperanta klavaro ?
-
Mi intencas instali la esperantan klavaron EK3.9, sed kiam mi volas elŝuti la softvaron, la antiviru…
-
07 Dec 2011
中华字经(四)
-
dì sì bù fēn
第 四 部 分
yòu zhì zǎo qiào wán shuǎ liàn xí tóu nǎo rèn niàn jué qín jiǎn x…
-
08 Apr 2011
See all articles...
Authorizations, license
-
Visible by: Everyone (public). -
Free use
-
2 007 visits
软枣
软 枣
——儿时对甜的记忆
文 /风颠
Jump to top
RSS feed- Latest comments - Subscribe to the feed of comments related to this post
- ipernity © 2007-2024
- Help & Contact
|
Club news
|
About ipernity
|
History |
ipernity Club & Prices |
Guide of good conduct
Donate | Group guidelines | Privacy policy | Terms of use | Statutes | In memoria -
Facebook
Twitter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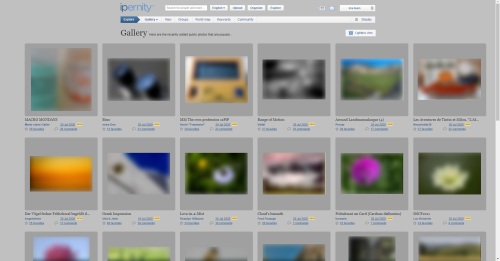
Sign-in to write a comment.